第一章 明天的寓言
美国的中心曾经有一个小镇,那里的所有生物看上去都与其周边的环境和谐共处。小镇的四周如棋盘一般分布着繁荣的农场,庄稼连成一片,山坡上果树成林,春天的时候山花烂漫,犹如朵朵白云在绿色的原野上飘荡。秋天,橡树、枫树和白桦树色彩斑斓,透过松林的绿色屏障,如火焰般跳跃着。小山上狐狸在鸣叫,小鹿悄悄地穿过田野,在秋天的晨雾中半隐半现。
路边生长着月桂树、荚莲花、赤杨树,还有巨大的蕨类植物和各种野花,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能让过路的行人赏心悦目。即使是冬天,道路两旁也有一番美景,无数的小鸟飞来,啄食浆果和露出雪地的干草穗头。实际上,这个乡村正是以生活着种类丰富的大量鸟类而闻名。每年的春天和秋天,迁徙的候鸟潮涌而至,人们会从很远的地方前来观赏盛景。也有人来小溪边钓鱼。澄澈而清凉的河水从山间流出,绿树掩映下的池塘里鳟鱼在游动。所以,很多年前,第一批人来到这里,掘井盖房,搭建谷仓。
突然,一种奇怪的力量悄悄侵袭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变了。一种邪恶的魔法控制了整个社区:鸡群感染了神秘的疾病;牛羊开始生病死亡。死神的阴影笼罩着每个地方。农夫们都在谈论家人的病况。镇上的医生也越来越困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近来病人的病症。大人出现毫无来由的突发性死亡。孩子们也未能幸免,他们在玩耍的时候突然发病,几个小时后就会死去。
每个地方都安静得出奇。那么多的鸟儿都去哪儿了?人们议论纷纷,感到困惑不安。院子后边喂食的地方冷冷清清。零星见到的几只鸟儿都气息奄奄,身子不住地颤抖,再也飞不起来。这是一个毫无声息的春天。往日的清晨,有知更鸟、猫鹊、鸽子、松鸦、鹪鹩的合唱,还有其他各种鸟儿的伴奏,如今却听不见一点声音;田野、林间、沼泽,到处是寂静一片。
农场里,母鸡下的蛋孵不出小鸡。农夫们抱怨没法继续养猪,因为猪崽都太瘦弱,存活没几天就会死去。苹果树就要开花了,却不见蜜蜂往来穿花的身影,所以花儿没有授粉,也就不会结果。
道路两旁,曾经是那么迷人的地方,如今一片枯黄,仿佛被火烧过一样。这些地方也是一片寂静,没有生命的迹象。甚至溪流都变得毫无生气。鱼儿都已死去,再没有人来钓鱼。
屋檐下的水槽里,屋顶上的瓦板间,仍能看到一片片的白色颗粒粉末。几个星期以前,这种粉末像雪花一样落在屋顶、草地、田野和溪流。
不是巫术,也不是敌人的行动侵袭了这个世界,让新的生命无法复生。一切都是人们自己造成的。
这个小镇并非真实的存在,但在美国或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却可能有上千个类似的地方。我还没有发现遭受上述全部不幸的地方。但是,其中任何一种灾难都已经在某个地方发生,而且有的社区已经遭受诸多苦难。一个恐怖的幽灵正悄悄向我们袭来,而且这个想象中的悲剧极可能变成我们终将面对的严峻现实。
是什么东西让美国无数的城镇失去了春天的声音?本书将试着给出答案。
第二章 忍受的义务
地球生命的历史是一部各种生命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地球植物和动物的形态与习性都是由环境造就的。就地球的全部时间而论,生物对周围环境的反作用却相对很小。随着时间的推进,尤其是到20世纪,人类获得了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
在过去的大约25年里,这种力量不仅强大到令人担忧,而且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人类对环境的侵袭最令人震惊的要数危险的甚至致命的物质对空气、土壤、河流以及海洋造成的污染。这种污染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恢复的;其在生物生存环境以及生物组织中引发的负面连锁效应也是不可逆转的。在当前环境遭受普遍污染的形势下,化学药品可以改变自然界及万物生命,与辐射一样危害巨大,只是尚未为人所知。核爆炸向空气中释放出的锶90,或随雨水进入土壤,或以放射性尘埃形式落在地表,进而被草、玉米或小麦吸收,最终进驻人类的骨骼中直至其死亡。同理,农田、森林以及花园里喷洒的农药会在土壤中长存,接着进入生物体内,在中毒和死亡的链条中不断地传递下去。它也可以随着地下水神秘地转移,通过空气与阳光的作用再次出现,并生成新的物质,毁坏植被,使牲畜生病,让曾经可以饮用纯净井水的人们遭受离奇的伤害。正如阿尔伯特·施韦泽所言:“人类甚至不认识自己创造的恶魔。”
经过了几百万年的演化,地球上才有了各种生物。在漫长的时间里,地球生物发展进化,物种逐渐增加,慢慢与周围环境达到了一种协调平衡的状态。自然环境极大地影响着生物的形态,指引生物的演进方向,包含了各种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一些岩石会有危险的辐射;甚至为万物提供能量的阳光中,也有可以造成伤害的短波辐射。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是几年,而是上千年时间,生物慢慢得到进化,与自然环境达成平衡。所以,时间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素,但是现代社会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时间。
与自然界精妙细微的演进相比,人类活动显得鲁莽而无知,带来的变化异常迅猛,新状况层出不穷。在地球上出现生命之前,就有岩石背景辐射、宇宙射线、太阳光紫外线等各种辐射。如今,人类研究原子的活动产生了新的非自然辐射。生物进化所要适应环境中的化学物质不再仅仅是钙、硅、铜以及河流冲刷岩石带入海洋的其他矿物质,又增加了人类在实验室创造出来的合成化学品,自然界中从来没有这些物质。
适应这些物质所需的时间要以自然历史的维度衡量,不仅仅是人生的短短几十年,而是多少代人的时间。即便奇迹发生,生物的确能够适应新的物质,一切也会变成徒劳,因为新的化学物质源源不断地从我们的实验室中产生;单在美国,每年会有500种新的物质投入使用。尽管这个数字令人惊愕,其后果却不易为人理解——人类与其他动物每年需要适应500种物质,远远超出了生物进化的极限。
这些化学药物大多应用于人类对自然的战争。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人类创造了200多种化学药物,用来对付昆虫、野草、啮齿动物以及其他现代语言中称为“害虫”的生物,而且这些化学品有数千种不同的品牌。
如今,这些喷剂、药粉和气雾剂被普遍地用于农田、花园、森林以及人们的院子里。未经选择的化学药剂可以杀死所有的昆虫,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可以使鸟儿不再唱歌、鱼儿不再畅游,可以在叶子表面覆盖一层致命的外衣,可以在土壤中长久留存。一切都仅仅是为了对付野草和昆虫。地球表面覆盖了一层毒药,谁会相信这不会对生物产生危害。这些物质不应被叫作“杀虫剂”,而应是“杀生剂”。
喷洒农药似乎卷入了一个无尽的循环。自DDT民用以来,使毒性升级的活动从未停止过。昆虫成功地证明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原则,它们通过进化产生了抗药性。因此,人类需要毒性更强的药剂,照此循环下去。另外,使用农药一段时间后,被消灭的昆虫会卷土重来,数量反而比之前更多。这种现象的原因会在后面解释。所以,人类从未赢得这场化学之战,而所有的生物却被卷入残酷的战火中。
除核战争可能毁灭人类外,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核心问题便是,具备强大潜在杀伤力的物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普遍污染。这些物质可以在植物和动物体内累积,甚至渗透进生殖细胞,破坏或改变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
一些自称人类未来工程师的人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设计、改变人类的遗传细胞。但是,如今我们可能由于疏忽大意而轻率地做了这样的事,因为很多化学物质会像辐射一样造成基因突变。人类可能通过使用杀虫剂这看似微小的举动,决定自己的未来,想来是有点讽刺的。
冒如此之大的风险,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为我们扭曲的判断力所震惊:为什么智慧的人类要通过污染整个环境、毒害动物甚至人类自身的方法,来控制一小部分自己不喜欢的物种。
然而,这正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还没有研究明白,就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专家告诉我们,杀虫剂的广泛使用是保证农业产量的必要措施。但是,我们的问题不正是“生产过剩”吗?尽管有减少农作物面积的措施和补贴农民不进行农业生产的政策,我们的农业产量仍然惊人。1962年,美国纳税人需要为剩余粮食支付超过10亿美元的储囤费用。农业部的一个部门试图减少产量,而另一个部门却在1958年宣称:“通常,在土地银行的规定下减少作物面积会刺激化学品的使用,以从现有耕地获得最大的产量。”状况改善了吗?
这并不是说昆虫不是问题,不需要加以控制。我想说的是,控制手段必须以现实为依据,而不是靠主观臆想,而且采用的办法必须不能把我们连同昆虫一起毁灭。
这一问题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个产物,刚要试着解决它就带来了诸多灾难。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就有各种昆虫在地球上生存,它们种类繁多,具备很强的适应能力。自人类出现以来,50多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开始以两种基本方式与人类福利产生冲突:争夺人类食物供给,传播疾病。
在人口较多的地区,尤其是卫生状况恶劣、自然灾害频发或极度贫困的条件下,携带病毒的昆虫是一个尤为关键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一些昆虫进行控制。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然而,正如我们目前所见,大量使用化学药剂的方法不仅限制了胜利的成果,而且可能造成试图控制的状况更加糟糕。
在原始的农业条件下,农民们几乎没有昆虫问题。随着农业发展,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各种昆虫问题开始出现。这种种植系统成了某种昆虫数量猛增的温床。单一作物的耕种方法只是工程师眼中的农业,并不符合自然的规律。自然界孕育了万千物种,然而人类却热心于将其简化。因此,他们破坏了自然界内在的制约与平衡机制,而大自然正是以这种方式控制各种物种。适宜每个物种生存的面积就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很明显,如果一片农场里只种植小麦,那么一种昆虫的数量就可以增加很多,以至于远远超出小麦与其他作物混种的地区,因为这种昆虫不能适应其他作物。
其他情况下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上一代或更久以前,美国大城镇的街道两旁都种上了高大的榆树。如今,他们希冀的美景不仅没有实现,反而面临毁灭的危险,因为甲虫带来的疾病肆虐了所有榆树。但是,如果榆树与其他植物掺杂点缀,甲虫不可能大量繁殖、蔓延。
现代昆虫问题的另一个因素必须在地质和人类历史的背景下审视:成千上万不同的生物从自己原来的生存环境扩张、蔓延至新的区域。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埃尔顿在他的新书《入侵生态学》中研究了这种全球范围的大迁徙,并作了生动的描述。在几百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汹涌的海洋切断了大陆间的陆桥,各种生物被困在了埃尔顿所称的“巨大的独立自然保护区”内。它们与同类的伙伴隔绝,开始演化出新的物种。大约1 500年前,一些大陆板块重新连接后,这些物种开始扩张到新的疆土。这一运动如今仍在进行,只是增加了来自人类的大力协助。
植物引进是现代物种扩张的主要原因,因为动物们必然会随着植物进行迁移。检疫只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不完全有效的措施。单单美国植物引进署就已经从世界各地引进了大约20万种植物。美国180种植物害虫中大约有一半是意外地从国外引进的,其中大部分是随着异域植物一起进来的。
到了新的地方,没有了自然界天敌的威胁,它们的数量不再受到限制,因此入侵的动植物会大量地繁殖。这样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昆虫问题就不再是偶然事件了。
无论是自然地发生,还是人为的帮助,这种入侵很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检疫和大规模地使用化学药剂不过是在拖延时间。如埃尔顿博士所言,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不仅仅是迫切地需要找到抑制各种动植物泛滥的科学方法”,我们还需要明白动物种群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这样才能“促成一种平衡”,抑制虫灾和新物种入侵的爆炸性力量。
很多必要的知识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从不去运用这些知识。我们的大学里有优秀的生态学专家,甚至政府部门也有,但是我们很少听取他们的建议。我们好像别无选择一样,任凭化学药剂的死亡之雨落下。而实际上办法很多,而且只要有机会,凭借我们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发现更多的解决办法。
我们是被什么东西迷惑心窍了吗?以至于好像失去了判断好坏的意愿和智慧,而逆来顺受地接受低劣和有害的事物。如生态学家保罗·舍帕德所言,这种思维就是“脑袋刚刚漏出水面就会觉得很满足,却不知离自身环境的崩溃只有咫尺之遥……为什么我们要忍受带毒的事物,忍受住所周围的死气沉沉,与各种不算敌人但又有威胁的动物共存,忍受快要让我们发疯的汽车噪音?谁会愿意活在一个仅让你只能算得上是活着的世界?
然而,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创造一个无菌、无虫害世界的运动,似乎引发了许多专家以及所谓管制机构的一阵狂热。从各个方面看,那些忙于推广农药的人们实际上是在滥用权力。“负责监督的昆虫学家扮演着检察官、审判官、陪审团、估税员、收税员和司法长官的多重角色,以实施他们的命令”,康涅狄格州的昆虫学家尼利·特纳说。在州政府以及联邦政府机构中,公然滥用职权的现象不受任何约束。
我并不是说完全不能使用化学杀虫剂。我要指出的是,我们任意地把具有强大毒性和生物影响力的化学品交到一些人手中,而这些人很大程度上或者完全不知道其潜在的危险。我们让太多人接触了这些毒药,而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甚至常常不去告知他们。《权利法案》中没有规定:公民不应受到致命毒药的威胁,无论是来自个人,还是政府官员。这只是因为,虽然我们的先辈拥有过人的智慧和远见,但也无法预见到这样的问题。
此外,我还要强调,我们很少或从未调查化学品对土壤、水、野生动物以及人类自身的影响,就允许它们投入使用。对于滋养万物的自然世界,我们未能给予足够谨慎的关切。将来,子孙一定不会原谅我们的。
人们对潜在威胁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的问题,而意识不到或不愿接受更广泛的层面。这也是一个受工业主宰的时代,不惜代价赚钱是不容批评的首要原则。当人们知道一些使用杀虫剂造成破坏的明显证据而进行抗议时,含着半真半假事实的镇定药片就会给他们服下。我们迫切地需要结束这种虚假的安慰,停止为丑恶事实裹上糖衣的行为。除虫人员造成的危害正在由公众承担着。人们必须决定,是否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当了解所有的事实后,他们有能力作出决定。正如吉恩·罗斯坦德所言:“忍受的义务给予我们了解真相的权利。
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25周年纪念版简介
——美国前副总统 阿尔·戈尔
作为一名民选的官员,为《寂静的春天》作序令我感到十分卑微,因为蕾切尔·卡逊的著作是一座丰碑,它证明了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加强大。1962年,《寂静的春天》刚出版的时候,公共政策里还从没出现过“环境”这样的词汇。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更多的是因为烟雾的出现,而不是对公众健康的威胁。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大会上提到了资源保护(环保主义的前身),但只是在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文本中顺便提及。除了一些很难见到的科学期刊上的零星刊登,几乎没人讨论DDT以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品日渐严重、不易察觉的危害。《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部著作,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迟很长时间,甚至现在都还没有开始。
本书作者曾是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一名海洋生物学家。不出意料,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人纷纷抵制作者和她的书。一些大型的化工公司企图阻止《寂静的春天》出版。《纽约客》上摘录了此书的片段后,马上有人指责卡逊是歇斯底里的、极端的女人。直到今天,问起那些从环境现状谋利的人们,仍会听到各种谩骂(1992年我竞选的时候,被人们叫作“臭氧人”,这可能不是一种赞美,但我却感到非常光荣。我意识到,提出这些问题会不可避免地激起猛烈的或是愚蠢的反应)。当这本书广为人知的时候,反对作者的力量变得更加可怕。
蕾切尔·卡逊受到的攻击与《物种起源》出版后查尔斯·达尔文的遭遇一样。此外,由于卡逊是一名女性,很多非议直接指向她的性别。他们称她是歇斯底里的女人。《时代》杂志指责她“煽情”。她的科学声誉也受到攻击:反对者资助各种宣传,企图否定她的研究。这些攻势凶猛、有充足财力支持的负面宣传不是针对一个政治候选人,而是针对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在这场战争中,卡逊体现出两种决定性力量:对真理的尊重和对个人事业的执着。她反复检查了《寂静的春天》里的每一段话。而且过去几年的状况已经证明,她的警告是很谨慎的。她具有非凡的勇气和远见卓识,决心撼动一项根深蒂固、有利可图的产业。在写作《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她忍受着乳房切除的痛苦,并接受着放射疗法。书出版两年后,乳腺癌夺走了她的生命。讽刺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种疾病与接触有毒化学品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卡逊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写作。
她的写作对科学革命早期形成的陈腐观念提出了挑战。人类(当然这里指的是男人)是万物的中心与主宰,科学史就是人类的统治史,最终达到一个近乎绝对的状态。当一名妇女对这种正统观念提出挑战时,著名的卫道士罗伯特·怀特·史蒂文斯的回应在今天看来不仅傲慢,而且像地球扁平理论一样奇怪。他说:“争论的焦点在于,卡逊女士认为人类的生存取决于自然的平衡,而现代社会的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逐渐控制了自然。”
以今天的眼光看,那种荒谬的世界观正表明蕾切尔·卡逊的观点多么具有革命性。大公司的攻击不难预料,但美国医学会竟然也站在化工公司的一边。发现DDT杀虫特性的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是,《寂静的春天》不可能被扼杀。虽然它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但是著作本身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卡逊之前的两部畅销作品《我们周围的海洋》和《海洋的边缘》不仅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还为她赢得了经济的独立和公众的信任。《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的10年是一段活跃的年代,美国人乐于接受书本中传递的信息。在某种意义上,卡逊是这场运动的开始。
最终,政府和公共部门也参与进来——不仅是看过书的人们,还有看到报纸和电视节目的民众。《寂静的春天》销售量超过50万本后,CBS为它制作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节目,尽管两家主要的赞助公司取消了赞助,他们还是坚持播出节目。肯尼迪总统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讨论了这本书,并指定一个专门的调查小组调查书中提出的观点。调查小组的报告书控诉了化学品公司和政府无动于衷的态度,并证实了卡逊关于杀虫剂潜在危害的警告。不久之后,国会开始举行听证会,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成立。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蓄积成为空前强大的力量。1964年春天,蕾切尔·卡逊去世后,一切都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沉寂。她唤醒的不只是我们的国家,而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环保运动的开始。
《寂静的春天》对我个人有着深刻的影响。我的母亲坚持让我们阅读这本书,并在餐桌上讨论。姐姐和我从来不喜欢在餐桌上讨论书本,但我们关于《寂静的春天》的讨论却非常愉快,至今记忆犹新。蕾切尔·卡逊的确是我关注环境、投身环保事业的原因之一。她的榜样激励我写下《濒临失衡的地球》。我的书自然也是在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的,因为他们一直站在卡逊这边,并出版了许多关于当前环境问题的好书,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我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她的照片,旁边是众位政治领袖、总统、国务卿的照片。她的照片已经挂在那里好多年,而它就应该挂在那里。卡逊对我的影响比得上墙上的任何一位,或者更多,甚至超过他们的总和。
作为一名科学家和理想主义者,卡逊是孤独的,她懂得倾听,而当权的人们却难以做到。马萨诸塞州达克斯伯里市的奥尔加·哈金丝给卡逊写了一封信,告诉她DDT杀死了鸟类,促使她开始构思《寂静的春天》。今天,由于卡逊的努力而禁止了DDT,她关心的一些鸟类(例如:鹰和游隼)不再处于灭绝的边缘。她的著作也可能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
《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两本书都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但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哈里特·比彻·斯托把为人熟知的、公众讨论的焦点问题写在小说里,把一个全国人都在关注的问题在人物身上体现出来。她刻画的奴隶形象触动了国人的良心。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亚伯拉罕·林肯接见斯托夫人时说:“你就是那位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相反,蕾切尔·卡逊所警告的危险没人看得到,她试图把问题提上国家议程,而不是为已有的问题提供证据。这样看来,她的成就更加来之不易。讽刺的是,1963年她在国会上作证时,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用奇怪的语气模仿了一个世纪之前林肯说过的话。他说:“卡逊小姐,你就是引发这一切的妇女啊。”
两本书的另一个区别体现在《寂静的春天》所具有的持续性。奴隶制是可以终结的,而且确实已经终结了,尽管一个多世纪之后人们才开始处理它带来的后果。签署一份文件就可以废除奴隶制,化学污染却不行。尽管卡逊提出了有力论据,尽管美国对DDT实行了禁令,但是环境危机没有改善,反而加重了。或许灾难发生的速度有所放缓,但仍令人心生不安。自《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仅用于农场的农药就增加至每年11亿吨,各种危险化学品的产量增加了400%。在国内我们已经禁止了一些杀虫剂的使用,但杀虫剂的生产和出口仍在继续。这不仅说明我们愿意向他人出售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以获利,还说明我们没有意识到科学规律的作用不受政治边界的限制。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受到污染,最终会殃及其他地方。
卡逊作过的演讲很少,最后一次是在全美园林俱乐部。她承认,如果不采取改善措施,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她说:“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她还警告说,我们等得越久,风险就越大。她说:“我们让所有的人面临着接触化学品的危险,动物实验证明这些化学品都具有很强的毒性,而且很多时候毒素会在体内累积。从出生,甚至出生之前,我们就开始接触化学品,如果不作出改变,对化学品的接触将贯穿我们一生。”自从她下了这些断言后,我们不幸地经历了很多例证,因为可能与杀虫剂相关的癌症和其他疾病发生率飙升。问题不是我们不作为。我们确实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环境保护署(EPA)成立于1970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蕾切尔·卡逊唤醒的关切和意识。杀虫剂监管机构和食品安全检查局从农业部分离出来后成立了新的机构。农业部往往只看到使用农药的好处,却容易忽视潜在的危险。从1962年起,国会不止一次地要求确立杀虫剂检验、注册和信息标准,但大部分标准都被忽视、推迟和废弃了。例如,克林顿—戈尔政府时期,还没有保护农场工人免受杀虫剂危害的标准,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环保署一直致力于确立安全标准。像DDT这样的广谱杀虫剂已经被毒性更强的窄谱杀虫剂取代,但它们并没有经过全面的检测,具有相当的甚至更大的危害。
多数情况下,杀虫剂工业中的强硬派已经成功地推迟了《寂静的春天》呼吁的保护措施。这些年来,杀虫剂工业仍受到国会的纵容,实在令人震惊。关于杀虫剂、杀菌剂、灭鼠剂的法规比食品和药品的标准宽松得多,而且国会故意增加了法规的实施难度。在制定杀虫剂安全标准时,政府不仅考虑它们的毒性,还会考虑它们的经济效益。这种模糊的考量增加了农业产量(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却可能导致更多的人患上癌症和神经系统疾病,而且把一种有害的杀虫剂从市场上清除需要5到10年时间。新型杀虫剂,即使毒性更强,只要比现有杀虫剂效果稍好,就会得到批准。
依我看,这有点“在低地住久了,因为一点点上升就会自满”的感觉。现有的体制就像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长远福祉,获取短期利益。我们有理由相信短期利益确实很短。许多杀虫剂并不能使害虫灭绝,也许在开始阶段害虫有所减少,但它们最终会通过基因突变而逐渐适应,这样杀虫剂就失去了作用。此外,我们只研究了杀虫剂对成人的影响,而忽略了更容易受到伤害的儿童。我们只是孤立地研究每种杀虫剂的效用,而没有研究它们之间的反应,而这正是我们的田地、牧场、河流中潜在的巨大危险。基本上,我们继承了一个法律与漏洞并存、行动与延误同在的体系,其表面往往难以掩盖政策失败的真相。
蕾切尔·卡逊告诉我们,过度使用杀虫剂与基本的价值观不符;杀虫剂最坏的情况是制造了她所说的“死亡之河”,最好的情况是造成轻微伤害却得不到任何长远收益。真正的结果是,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的22年里,法律、监管和政治体系没有作出足够的回应。卡逊不仅熟悉自然环境,也深谙政治世界的门道,她已经预料到了失败的原因。在几乎没人讨论利益与权势的两大污染时,她在园林俱乐部的演讲指出,“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们占尽了利益”。她指责了政府为游说费用减税的政策(本届政府力图废除这一政策),她指出:“减税意味着化学工业能够以低廉的成本阻止相关立法……化学工业本就希望没有法律的束缚,现在如愿以偿了。”卡逊的谴责为当前政治改革的讨论埋下了伏笔。简言之,她准确地预测到政治才是问题的症结。要清除污染,就要理性政治。
一种多年来努力的失败可以解释另一种失败。结果不可否认,也令人难以接受。1992年,美国使用了22亿磅杀虫剂,相当于每个人承受8磅。我们知道许多杀虫剂是可以致癌的,其他一些杀虫剂则会毒害昆虫的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人类也可能受害。卡逊在书里提道:“我们可以在地板上打上一层蜡,经过的昆虫必死无疑。”虽然我们已经不再使用这种日用化学品,但今天超过90万个农场和6 900万个家庭在使用杀虫剂。
1988年,环保署报告说,已经有32个州的地下水受到74种不同的农药污染,其中包括除草剂阿特拉津,这是一种可能使人类致癌的物质。每年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玉米地使用7 000万吨阿特拉津,150万磅径流流入2 000万人的饮用水源。城市饮水厂无法清除阿特拉津;春天的时候,水里的阿特拉津含量常常超出安全饮用水法规定的标准。1993年,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25%的地表水都是这样。
由于其他原因,DDT和PCBs已经在美国被禁止,但是与雌性激素相仿的杀虫剂又大量出现,并引起人们新的担忧。苏格兰、密歇根州、德国以及其他地区的研究表明,它们可以导致生育能力下降,引发睾丸癌、乳腺癌和生殖器官畸形。单在美国,雌性激素杀虫剂泛滥的20年来,睾丸癌的发病率就增加了50%。虽然原因尚不明确,证据显示世界范围内的精子数已经下降了50%。这些化学品能够破坏野生动物的繁殖能力,证据确凿,不可辩驳。3名研究人员检查过《环境卫生研究院杂志》的数据后总结道:“现在很多野生动物种群正面临危险。”很多问题都预示着动物和人类的生殖系统将发生巨大而不可预测的变化,但是当前的危险性评估并没有考虑杀虫剂的潜在危害。新政府建议进行这样的检测。
这些化学品的卫士无疑会作出传统的回应:在人类身上的研究没有发现化学品和疾病的直接关联;巧合不等于因果关系(尽管一些巧合强烈地要求作出谨慎的决定,而不是鲁莽行事);动物实验的结果并不一定适用于人类。这些回答让我们想起了蕾切尔·卡逊从化工工业及其资助的大学科学家得来的回应。她早已预料到这样的回应,并在《寂静的春天》里写道:“公众服下了掺着半真半假事实的镇定药片。我们迫切地需要结束这种虚假的安慰,停止为丑恶事实裹上糖衣的行为。”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詹姆斯·瓦特在内政部任职、安·戈萨奇在环保署任职的时候,对环境的无知达到了顶峰。毒害环境的行为竟然被当作既精明又经济的务实主义。例如,在戈萨奇的环保署,杀虫剂的替代方案——病虫害综合治理(IPM)被当作异端处理。环保署禁止相关书籍出版,IPM方法的证书被认定为非法。
克林顿—戈尔政府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观点,并决心扭转杀虫剂污染的潮流。我们的政策遵循三个原则:更严格的标准、减少使用化学品、更多地用生物制剂替代。
显然,明智的杀虫剂使用方法要平衡危险与利益的关系,并考虑经济因素。但是我们也要排除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标准要明晰而严格,检测要全面而可靠。长久以来,我们设立的儿童杀虫剂残留容忍值一直是应有水平的几百倍。怎样的经济效益才能证明其合理性?我们不仅要检测化学品对成人的影响,还要检测对儿童的危害。不同化学品组合的效应也要检测。检测化学品不仅是为了减少恐惧,更是为了减少必然会令我们恐惧的东西。
如果不需要使用杀虫剂,或者杀虫剂在特定条件下会失效,就不应该使用它。必须有真真切切的效益,而不是可能的、暂时的或猜想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关注生物制剂的发展,尽管它饱受化工工业及其政治辩护人的敌视。在《寂静的春天》里,卡逊提到了“真正神奇的昆虫化学控制方法的替代方案”。这种替代方法很多,尽管很多官员漠不关心,生产商百般阻挠。为什么我们不去推动无毒物质的使用呢?
最后,杀虫剂生产和农业是一边,公共健康是另一边,我们必须在两种文化之间搭建桥梁。两个群体有着不同的背景,读的是不同的大学,有着不同的观点。只要他们在怀疑和憎恨的鸿沟边对峙,对我们而言,改变生产和利润依赖污染的体制就难以改变。通过让农业推广局推广化学品的替代方案,我们可以开启终结旧体制的道路,并开始缩小文化鸿沟。另一种办法是让食品生产者和保护我们健康的人们保持正式的、持续的协商。
克林顿—戈尔政府关于杀虫剂的新政策有很多设计师。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一名妇女。1952年,她从中层公务职位辞职,全身心投入写作。卡逊的精神指引着本届政府所有重要的环境会议。可能我们无法立即达到她的期待,但我们正沿着她的指引前进。
1992年,一个由杰出的美国人组成的小组评选《寂静的春天》为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在过去的那些年以及所有的政策辩论里,这本书一直是控制自满情绪的理性声音。它不仅使工业和政府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还唤醒了公众的环境意识,它把民主的力量注入拯救地球的事业。渐渐地,即便政府没有行动,消费者也会自觉地抵制杀虫剂污染。现在,减少食物中杀虫剂残留不仅仅成为推销的手段,而且已经变成道德上的责任。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但民众自己也可以作出决定。我坚信,民众不会再纵容政府无所作为或作出错误的决策。
蕾切尔·卡逊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寂静的春天》里所提出的关切内容。她让我们重拾在现代文明中几乎消失殆尽的基本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融合。这本书就像一道光亮,照向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在《寂静的春天》的最后几页,卡逊借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里“少有人走过的路”,描述了我们要作的选择。一些人已经走上那条路,但很少有人像卡逊一样领着世界前行。她的辛劳、她揭示的真理以及她激发的科学与研究,不仅是限制杀虫剂使用的有力论据,也是个人能够创造巨大价值的有力证明。
致 谢
1958年1月,奥尔加·哈金丝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她生活的地方已经变得毫无生机。我的思绪立即被拉回到我曾一直关注的问题。考虑过后,我觉得有必要写下这本书。
自那时起,我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和鼓励,在这里无法逐一列出他们的名字。那些曾无私地与我分享他们多年经验和研究成果的人们,有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机构的,有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也有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在此我向所有人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你们慷慨地付出时间和分享智慧。
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花费时间阅读本书手稿并运用专业知识提出建议和批评的人们。虽然,我对本书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承担最终责任,但是,如果没有以下诸位专家的慷慨帮助,我不可能完成这本书。他们分别是:梅奥医院的医学博士巴塞勒谬(L.G. Bartholomew),德克萨斯大学的约翰·比塞尔(John J. Biesele),西安大略大学的布朗(A.W.A. Brown),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市的医学博士莫顿·比斯金德(Morton S. Biskind),荷兰植物保护署的布雷约(C.J. Briejer),罗伯和贝西·维尔德尔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克莱伦斯·科塔姆(Clarence Cottam),克利夫兰医院的医学博士乔治·克莱尔(George Crile, Jr.),康涅狄格州诺福克市的弗兰克·艾格勒(Frank Egler),梅奥医院的医学博士马尔科姆·哈格雷夫斯(Malcolm M. Hargraves),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医学博士休伯(W.C. Hueper),加拿大渔业研究委员会的克斯维尔(C.J. Kerswill),荒野保护协会的奥洛斯·穆里(Olaus Murie),加拿大农业部的皮科特(A.D. Pickett),伊利诺伊自然历史研究所的托马斯·斯科特(Thomas G. Scott),塔夫托卫生工程中心的克莱伦斯·塔泽维尔(Clarence Tarzwell),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J. Wallace)。
每一个作者,要写一本基于大量事实的书,都离不开图书管理员的知识和帮助。我也要感谢许多图书管理员的帮助,尤其是内政部图书馆的艾达·约翰斯顿(Ida K. Johnston)和国家卫生研究所图书馆的西尔玛·罗宾逊(Thelma Robinson)。
本书的编辑保罗·布鲁克斯(Paul Brooks),多年来一直给予我鼓励和支持,并甘愿多次推迟出版计划。对此,以及他优秀的编辑才能,我将永远心存感激。
在繁杂的资料搜寻工作中,桃乐茜·艾尔格(Dorothy Algire)、杰尼·戴维斯(Jeanne Davis)和贝蒂·达夫(Bette Duff)都作出有力贡献。写作过程中困难重重,如果不是我的管家艾达·斯波(Ida Sprow)的悉心照顾,我也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
最后,我还必须感谢许多与我不相识的人们,是他们让这本书变得更有价值。正是这些人率先站了出来,反对那些不计后果、不负责任地毒害世界的行为,保护人类和其他生物共同的家园。直到现在,这些人仍然在战斗着。他们的义举终将获得胜利,理智与常识也会在我们的世界得到传播。
蕾切尔·卡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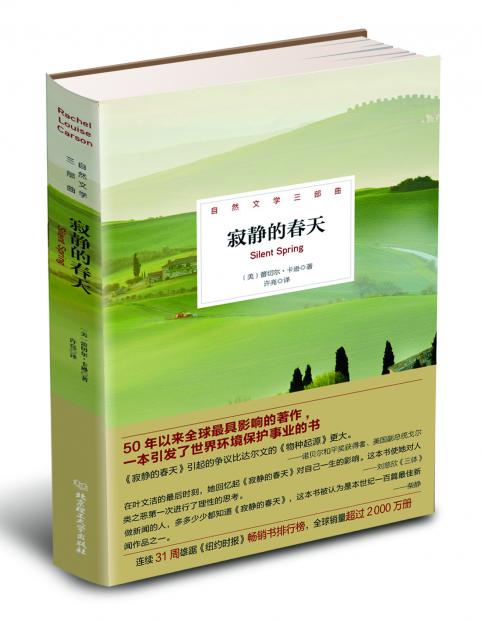
书名:寂静的春天
作者: (美)蕾切尔•卡逊
译者:许亮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